网络暴力治理所呈现的困境,关涉的是复杂社会的有效治理如何可能的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的社会性与时代性,决定了思考对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不能只着眼于刑法的视角,而必须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中来合理定位刑法的角色。笔者主要以网络暴力中的侮辱性、诽谤性言论作为关注对象,尝试探讨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有效治理,现行法律机制及其刑法与相应理论需要往什么方向发展。
传统言语暴力的基本特性与救济机制
传统线下社会的言语暴力与刑法层面对言语暴力的处理,有其社会现实方面的基础。首先,从加害—被害的关系来看,传统的言语暴力几乎是发生于存在特定关系的熟人之间,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其次,从传播范围来看,由于传播媒介与方式的限制,传统的言语暴力传播范围较为有限,通常局限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再次,从危害范围与程度来看,受害对象具有特定性,相应言论在侵害特定个体权益的同时一般不至危及社会利益,且危害程度较为可控。最后,从救济渠道来看,主要依靠私力救济而非公力救济。无论是提起民事侵权的诉讼还是启动刑事自诉的程序,都谈不上对受害方的维权构成重大妨碍。
传统言语暴力的确定性与可控性,使得法律尤其是刑法的扩大介入并无太大必要。法律层面的追责与救济仅作为特殊渠道存在,并以私人执行机制为基础。其一,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的关系来看,私力救济构成一般的常规,法律层面的公力救济则作为例外而存在。其二,启动法律层面的追责与救济的权利被归于私人,是否启动相应程序依赖受害一方的自主决定,过程中受害一方有权随时终止程序的进行。其三,无论是通过民事侵权的救济还是借助刑事诉讼的追责,都采取的是回溯性的视角,关注的重心在于已然发生的行为。由是之故,民事侵权的诉讼以填平损害为原则,刑事诉讼则采取惩罚主义而非预防主义的立场。
传统言语暴力的处理并不倚重法律,根源于线下社会人们在场式的互动方式,在场空间等同于社会空间;建立在私权模式之上的民事侵权与刑事自诉的相关制度,乃是与其所调整领域的存在论特性相契合的救济举措。同时,刑法上对传统言语暴力的治理采取私权模式,与古典法律体系中“社会”的缺席有关,也与彼时对政府角色的设定有关。
网络暴力作为社会压制的体现与根源
虚拟网络空间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空间的基本结构与人际之间的互动机制。海量用户的“在场”与交互相动,极易引发类似于黑箱的系统性效应,即混沌与涌现的现象,不仅私人问题容易被公共化,也易于形成浪潮或海啸般的指数级传播。同时,作为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网络空间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权力结构与支配关系。网络暴力的生成与网络空间的结构特性和网民群体的互动机制直接相关。
当代社会理论敏锐地洞察到,个人不仅受到来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压制威胁,也面临源自社会的压制危险。网络暴力本质上是社会性压制的体现。此处的社会性,不仅意指加害主体是匿名化的大众,且借助的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更意指网络暴力根源于社会系统的宰制,带来类似于韦伯说的理性化危机,导致个体自由被系统理性吞没从而受困于系统性权力的支配,陷入理性化的铁笼之中。一方面,网络暴力的生成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能与匿名运作机制有关,而匿名运作机制下的技术赋能本身就会带来对个体自由的全新威胁。另一方面,网络暴力的加剧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及法律系统未能合理解决相应社会问题有关。
网络暴力与私权模式法律机制的脱节
网络暴力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系统性的力量对个体的压制,属于一种新型的支配关系形式。其一,从加害—被害关系来看,网络暴力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表现为具有自组织性的群体在网络上针对个人实施的言语性攻击,不仅加害主体的范围具有动态性并不确定,而且双方之间处于明显不平等的地位。其二,从传播范围来看,借助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媒介,网络暴力易于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蔚然成势,产生超越地域甚至超越国界的历时性影响,表现出极为鲜明的时空延展性。其三,从危害范围来看,除特定个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外,网络暴力往往还同时影响到重要的公共性法益;就危害程度而言,网络暴力的危害远较传统的言语暴力要严重。其四,从救济渠道来看,被害一方既难以依靠自力救济来保护自身权益,也难以在法律层面展开有效的追责。
由于网络暴力代表的是社会的系统性力量对个体施加的侵害,相应便会出现法律救济机制与社会现实基础相脱节的问题。无论是民事侵权诉讼还是刑事自诉程序,举证问题都成为个体通过法律进行维权时的不堪其负之重。更何况,受害者面临的困境还在于救济措施无法消除社会影响,根本不足以弥补网暴所造成的侵权后果。私权模式的法律机制由于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个案的事后救济之上,会导致对网络暴力的事前规制与预防乏善可陈,更难以对公共性的利益展开有效的保护。网络暴力的处理困境,也折射出公法与私法的二分体系无法延续的事实。这种二分体系受到冲击,乃在于古典法律体系的构造中缺乏“社会”的维度。
网络暴力治理中法律机制发展的方向
有必要在“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结构中,来考虑刑法上如何应对网络暴力的问题。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不仅要承担不得过度干预个人私域与相应自由的消极义务,也要承担使个人免受社会性权力不当侵害的积极义务。国家对个人的消极义务是传统公法主要关注的命题,应对的是国家作为可能的侵害者的场景;国家对个人的积极义务则在“社会”崛起之后日益受到关注,处理的是社会作为可能的侵害者的情形。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以保护个人免受社会性权力的不当侵害。与此相关的应对举措,一方面表现为对弱势的个人进行积极的赋权,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性主体施加各类合规义务。
法律体系由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转变以及对国家双重保护义务的强调,代表的是社会治理基本框架层面整体性的发展走向。其间的启示在于:首先,鉴于在网络暴力中社会本身成为对个体自由的侵害来源,私权模式的法律机制无力给予有效的救济,有必要转而采取以公力救济为主导的法律机制。其次,以公力救济为主导的法律机制,关注重心需要放在预防性举措的设置之上,而不是事后的责任追究与赔偿。最后,以谦抑为名要求刑法对网络暴力尽量不予干预的立场存在疑问,有必要适度扩张刑法的介入范围,强化对加害方刑事责任的追究。以威胁言论自由为由而反对刑法适度扩张的观点存在疑问。不能因为国家与平台在消极保护义务方面履行有亏,反过来论证二者也无需履行对个人的积极保护义务。
刑法体系立法与司法层面的相应调整
对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采取以事前预防为主的风险规制法的模式。这种事前的预防,要求注重法律体系的预防机制与其他治理手段的预防机制相结合,注重法律体系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有必要考虑引入领域法的做法,即立法上出台专门的立法,以便形成能够具有整合性效果的包含事前规制与事后追责的系统性机制。对于侮辱罪、诽谤罪的立法也需考虑作相应修正。单纯借助解释论的路径,即对有关告诉才处理的规定重新进行理解,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相关罪名所面临的挑战,采取立法修正的方式显得更为合理。可考虑分两款规定两档法定刑,情节严重的设置为告诉乃论,赋予被害人自主选择自诉或公诉的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幅度,并按公诉程序处理。
从司法适用来说,有必要依循功能主义的解释论立场,将刑事政策上的一般预防因素整合到解释的过程之中,以期有效提升罪刑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指引作用。据此可得出三个推论:其一,刑法对网络暴力犯罪的打击,应当根据所涉场景与行为对象作区分性的对待。涉及公共领域或公共人物的情形,刑法的介入必须节制与慎重;涉及私人领域与普通个人的情形,刑法对受害方个人权益的保护需加强。其二,在现行刑法对侮辱罪、诽谤罪作为亲告罪的规定未作立法修改的情况下,可考虑将“告诉的才处理”中的“告诉”理解为同时包含自诉与公诉,并赋予被害方自主决定是选择走公诉还是自诉的权利,以期在加强对个体权益保障力度的同时,提升刑事制裁的确定性。其三,在如何限定追责主体范围与如何判断行为的刑法性质及其程度的问题上,有必要在兼顾需罚性与应罚性的基础上,对法教义层面相关具体问题作出针对性调整。(劳东燕)
(原文刊载于《政法论坛》202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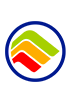 华光软文
华光软文
 发布于 2025-01-10
发布于 2025-01-10